《太岁志》作者刘向阳与粉丝聊创作过程
刘向阳,河南籍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太岁志》、神话史诗《格萨尔》和英雄史诗《渥巴锡》。日前,刘向阳在线回答粉丝提问,现整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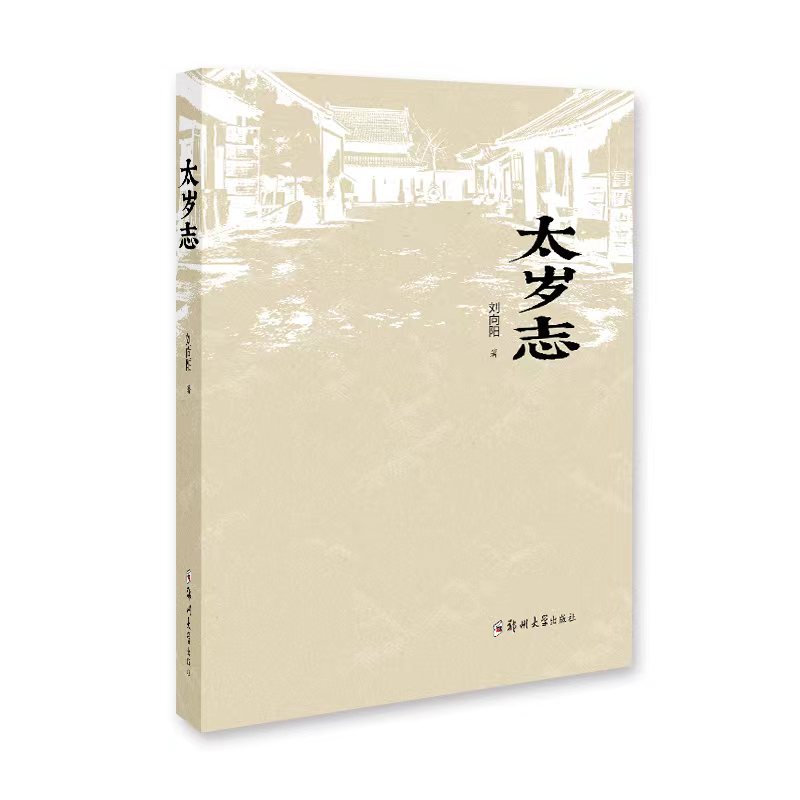
问:《太岁志》的人物原型来自哪里?
答:先看一段:日头将沉,辛丑乏了,喊道:“奶奶,吃杏!”奶奶在树下纳凉,说:“等来个人儿吧。”娘儿俩就等着。一会儿从南边悠悠来了个人儿,总是个子高高的,戴着泛白的草帽,肩着农具,脚后跟着地一步一步地踱过来。奶奶站起来冲那人说,大兄弟,俺小孙子想吃杏哩,恁给俺跺一脚吧。那人并不搭腔要么嗯一声,放下农具,粗糙的手指捏着草帽沿儿,仰着脸,绕着杏树转一圈儿,看准某处一脚跺上去,杏扑簌簌地落下。嫌少,那人再转,再跺一脚,杏又扑簌簌地落下。奶奶说,中啦中啦,恁拾点儿吃吧。那人并不拾,戴上草帽,肩上农具,悠悠地走了。
我的祖母就是“奶奶”这个。闹着吃杏的“辛丑”,就是我自个儿的童年影像。
确切地说,《太岁志》中家族史的素材占比多达30%。
问:《太岁志》的创作动机?
答:2012年,我本着记录家族史的动机落笔,结果下笔就到了十几万字的体量。我想,能否走得更远些?
2016年10月,五十万字的《太岁》初稿送到出版社。责任编辑邵大姐问我:你评职称用吗?我反问:谁拿小说评职称啊?她再问:哪你为啥写?我再答:我写得好。
邵大姐再问:“你愿不愿把《太岁》再扩十万字?”
多少文字能写尽这片土地的荣耀和秘密?多少句读能概括逝者的挣扎与徒劳?
我摇头道:不!
2018年12月,邵大姐通知我:稿子没过。
那时节我正埋头修改神话史诗《格萨尔》。没过?那就澄一澄呗。
五年之后,2022年12月25号,好日子,澄清了,稿子过了。不过,《太岁》得改名《太岁志》。
问:《太岁志》是现实主义的路子吗?
答:神话史诗《格萨尔》让我像浪漫主义者,英雄史诗《渥巴锡》贴上英雄主义的标签,那么,文化冲突的主题让《太岁志》被现实主义定义了吗?
哪有那么多劳什子的主义?我就是个口述者,执拗地宣示着爱与自由。
毕竟,我热爱这片土地,我心疼这些生灵。
问:能否聊聊《格萨尔》《渥巴锡》和《太岁志》的创作心得?
答:在《太岁志》里,我大胆使用了三种以上的叙事方式。
我自认首创并使用了“糖葫芦”式的叙事手法:主人公辛丑的经历仿佛一根穿过诸多人物和事件的签子。这根签子穿到哪里,角色和事件就像山楂,及时出现在合适的位置。另外,整部小说里,叙事视角至少变换了两次,书中不但有一以贯之的第三人称,也尝试了两个章节里两个角色的第一人称的自述。这样叙事或许会让阅读体验更多面更丰满。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李约翰》那一章,完全采用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问:您觉得作家在当下如何把握素材和创作?
答:《圣经》中的天使分为三阶九种,最高级的炽天使负责和神沟通,一众天使的职责就是赞美神。我一直纳闷儿:为什么天使是美丽的、而恶魔是丑陋的?这样的人设不利于教义的传播啊。反过来不好吗?恶魔是美丽的,才能蛊惑人心,才可能诱惑陷入歧途的罪人出卖灵魂啊。你看东方神话里,妖魔鬼怪的人设就是妲己、褒姒这样的绝世美人儿。
责任编辑:张思瑶
新闻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