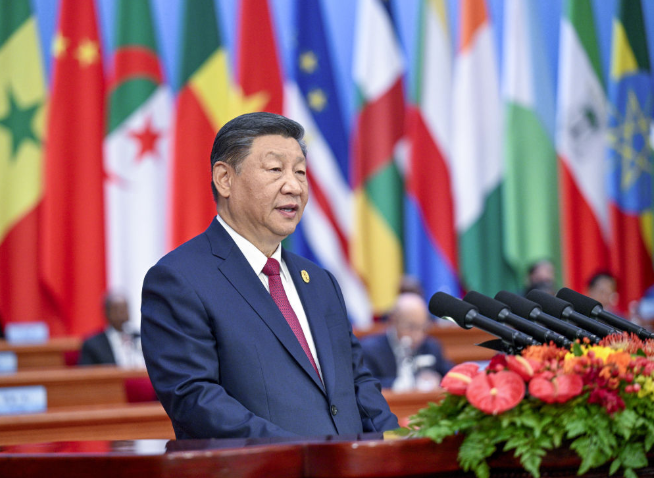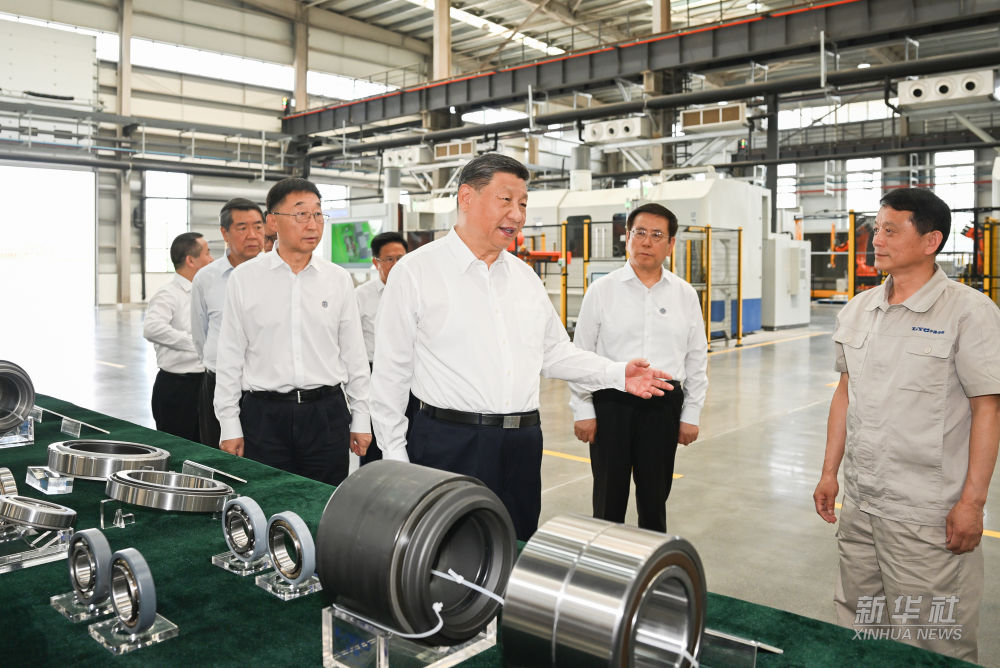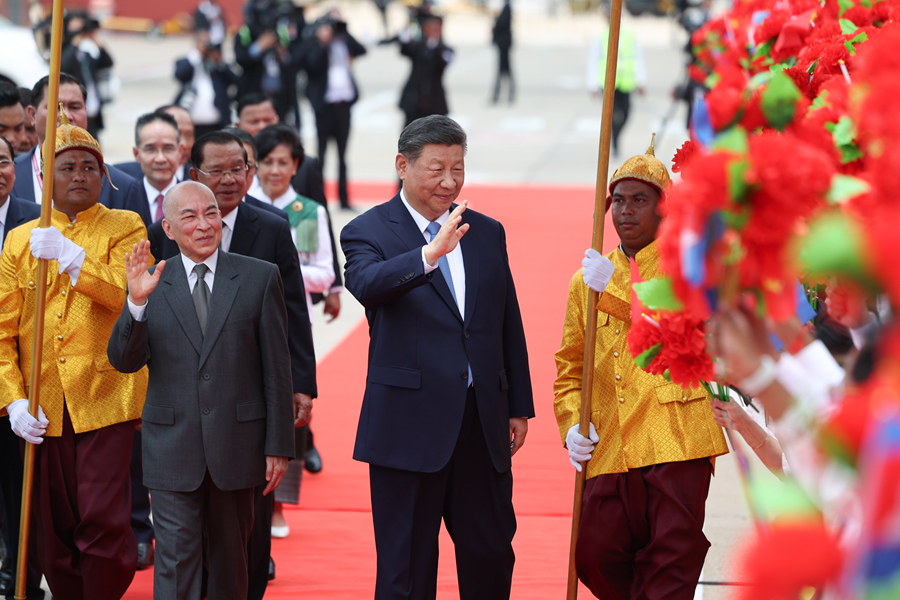新爱莲说
引 子
那儿的染料能当饮料喝,藕可以发酵成酒,荷花宴色香味俱全;那儿的风光水天一色,有鱼翔浅底,也有鸟飞长空;那儿的村姑心灵手巧,插花、刺绣、印染,把老宅老屋装点成低调奢华有内涵的民宿;那儿还有一群人见人夸的大嫂,齐力脱贫攻坚,共同增收致富,联手托举起村庄的大半个天空……

民宿一角。
那儿是韩徐庄村。
未见其村,先闻其详。在前往韩徐庄的路上,范县县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李博说起那儿的人文景观,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不过,”他稍微有些遗憾地说,“眼下已经入冬,看不到那儿的‘映日荷花别样红’了。”
“夏花灿烂,”陈庄镇宣传委员魏玉巍接过话茬儿说,“冬花傲骨。咱这时候去,正好‘留得枯荷听雨声’。”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韩徐庄被连片的荷塘包围,因莲而富,因莲而出名,因莲而赢得荷乡、荷花小镇等美誉,进而成为网红打卡的美丽村落。它偎依在黄河大堤脚下,东临国家3A级景区中原荷花园,北枕汤台铁路与濮台公路,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村子不大,共有158户620人,耕地700亩。截至2018年年底,建档立卡贫困户共41户161人。2019年9月,韩徐庄整村实现精准脱贫。
“来俺韩徐庄,”韩徐庄村新任党支部书记韩洪甫说,“应该先去看看俺村的不染工坊。”
范县是我省2021年村(社区)“两委”换届试点县。先行一步,韩洪甫已于11月8日履任现职。他今年32岁,种了5公顷稻子,收入逾10万元。魏玉巍打电话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在地里忙碌,此刻赶来,脸上头上满是汗,靴子上裤子上满是泥巴草屑。魏玉巍笑着问他,以后当一把手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种地了?“那哪能,”他有些腼腆地说,“我还准备多种点地,给大家带个好头。像俺老支书那样,事事干在前头。”
不染工坊坐落在村子西头,既是豫北荷乡民宿接待室,也是一个游客体验活动室。几个游客正饶有兴味地在不同的工序上忙碌。他们面前的储物筐里,是已清洗过的莲蓬、莲叶、莲子壳等。家在此地的李梦媛是一个在读大学生,来此实习两三个月了。她说,在韩徐庄,这些东西随处可见,以前都遗留在田间地头,或者当柴火烧掉。现在,它们登堂入室,成为弥足珍贵的天然染料原材料。冒着袅袅热气的染锅,正在让它们变废为宝。
李斌是北京大地乡居派驻韩徐庄民宿项目部经理,就在不染工坊办公。他说,我国印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染料染色的国家之一,利用植物染料也是我国古代染色工艺的主流。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在刀耕火种的过程中发现,草木的根茎叶皮,以及果实果核等,会在水和气温的浸渍作用中变色,并可从中提取染液。又进而发现,把这些花花绿绿的染料涂到脸上身上,既可以互相娱乐,也可以恐吓野兽,甚至可以在领地之争中出奇制胜。于是,染料的提取技术渐趋成熟,应用范围日益广泛。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来自荀子的《劝学》:“青,取于蓝,而青于蓝。”我知道这句话的引申意义,是说学生向老师学习超过了老师,后人继承前人超过了前人,本对其本意则不求甚解,只不过在人云亦云。今天得知,它直接来自人们对天然染料的认知:青(靛青)这种染料是从一种叫蓼蓝的草里提取出来的,但颜色比蓼蓝更深。可见在遥远的战国时期,天然染料提取技术已相当娴熟和普及,并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形而上学的意味。
整个染房暗香浮动,大自然的气息沁人心脾,沉浸其间,顿觉神清气爽。在裁剪、折花过程中,李梦媛和另一位叫吴桂花的女工指导着游客将纯白色的一匹亚麻布料裁剪成或长或方的条条块块,再把它们折叠出莲花、月牙、鱼儿、莲蓬等不同的花样,放入染锅,继续控温煮染。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不过二三十分钟,白布进去,花布出来,让人眼前为之一亮。那些披上沉静绿色、温暖黄色、热情茶色、凝重黑色的莲花、月牙、鱼儿、莲蓬,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俨然一件件艺术品了。
天然染料制作过程缓慢,染色过程精细,在化工染料一统天下的今天,一度濒临失传。所幸的是,这一古老的工艺又在韩徐庄焕发出绚丽的色彩。李梦媛说,前几天,她和几个小伙伴染了十来条丝巾,刚挂到网上就被抢购一空了,过几天准备再多染几条。吴桂花也说,上个月,她给贵州老家刚出生的侄孙子寄了一套自己浸染的衣服,老家的人都说好。天然染料浸染的衣服,健康环保没怪味,不伤害身体,最适合婴幼儿穿。不过,眼下的荷叶已染不出夏天荷叶的青翠碧绿,要看,只能去前面的那几座民宿里看看以前的染品。
民宿里果然别有洞天,宽敞明亮,纤尘不染。这儿斜插着一枝枯荷,那儿悬挂着一只荷包,风干的莲蓬置于案头,经霜的芦苇立在窗前,显得随意而匠心、宁静而致远。李斌说,这样的民宿共9套,客房17间,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北京大地乡居为韩徐庄投建的富民助农项目,旨在拓宽群众就业门路,助推乡村旅游发展。他说,眼下是旅游淡季,民宿入住游客不多。但一到节假日,房间就明显不够用了。
“现在看起来像模像样了,”韩洪甫说,“以前这几座民宿可都是透风漏雨的破屋。”
2018年12月6日至17日,作为范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结对帮扶单位,中石油牵手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北京大地乡居,启动针对韩徐庄留守妇女量身定做的“荷乡能工计划”,邀请全国知名的花艺、布艺、荷叶染工艺师来不染工坊授课培训。吴桂花是第一个报名参加培训的人。她说,通过培训,大家在掌握一技之长的同时,也陶冶了情趣,提升了品位,提高了在平凡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吴桂花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一双手,原来也不是只能摸农具、厨具,还可以摸到曾八竿子打不着的艺术,并可以靠自己的一双手脱贫致富。
吴桂花的家就在附近,与此只隔着两条胡同。她是韩徐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丈夫在天津打工,婆婆常年卧病在床,三个孩子小。收入少,开支大,一大家人的吃穿用度,怎么调配怎么不够,真应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句老话,时光一度很难熬。村里建了民宿,她和另外8名留守妇女来这里当管家,既可兼顾家里,也不影响打理民宿,间或绣点染点小饰品,请李梦媛捎带着挂到网上卖,一个月有两千元左右的收入。2018年年底,吴桂花成功脱贫,并被评为村里的孝善敬老标兵。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贝。韩徐庄对于莲蓬、莲叶、莲子壳的回收利用,对于危旧房屋的改造,再次为这句至理名言作出生动形象的注脚。
生生无限意 只在苦心中
莲藕浑身是宝,韩徐庄人深得个中三昧。离开染房,一阵酒香扑鼻而来。韩洪甫说,这是韩洪振藕酒坊里的香味。韩洪振的家庭虽然也曾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但他不同于一般的贫困户,有知识,有学历,有技术。他今年37岁,2006年从陕西国防学院毕业后,曾在烟台科奥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和精馏车间工作了5年。后来,他父亲患上心肌梗死等疾病,才返回老家,就近在河南丰利石化有限公司工作。尽管给父亲看病前后欠下十多万元的债务,但他不等不靠不要,一有闲暇就潜心研发藕酒制作工艺。2019年3月,他的藕酒制作工艺成功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8月,他的韩舍藕曲酒正式生产销售。韩洪振说,藕酒填补了国内白酒的一项空白,前景广阔。但在办理白酒作坊备案证的过程中,历经曲折,简直比制酒的过程还烦琐。白酒及酒精属于国家限制产业,国家经贸委第14号令《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目录》明确,1999年9月1日以后注册登记的白酒企业,不予受理生产许可证申请。多亏老支书韩保领、驻村第一书记郭自红、镇长李鹏宇等人认可他的酒艺,帮着跑前跑后,终于申领成功。据说,这也是自1999年9月以来,我市白酒行业申领成功的第一份白酒作坊备案证。
酒坊里热气蒸腾,浓郁的酒香挥之不去。韩洪甫说,藕酒属兼香型白酒,一酒多香,后味回甘,好喝不上头,在当地已得到普遍认可和好评。他去走亲戚或家中来亲戚了,就来这里买酒。这个酒坊的投产运营,不仅延长了村里的莲藕产业链,还吸收4个贫困户来此务工。韩洪振说,有一年,陈庄镇全镇莲藕大获丰收,供过于求,很多藕农找不到销路。他就是从那个时候萌生了研发藕产品的想法,作为新时代的农家子弟,不能让父老乡亲流了汗水再流泪水。现在,他的酒坊规模还小,只能年消化利用二三十万斤藕,但也有效缓解了街坊邻居的藕销售压力。来年他准备扩大规模,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
正说话间,一个骑着电动车的人来买酒,说家里来了客人,指定要喝藕酒。韩洪甫、韩洪振忙迎上去说,你打个电话让人送去就行了,还跑来干啥。
这个人就是刚卸任的老支书韩保领。
韩保领今年66岁,经历颇为传奇。在村人眼里,他打小认干,肯吃苦,有思路。17岁那年,年纪轻轻的他便挑起生产小队队长的重担,两年后兼任大队民兵连长。韩保领说,以前的韩徐庄像大多数村庄一样一穷二白,甚至比别的村庄更穷。因系背河洼地,饱受水患之苦,土地里只长盐碱不长庄稼,指望土里刨食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早在当生产队长时,他便带领大家搞副业,建了个暖房,孵小鸡小鸭小鹅。然后,与队里的年轻人一起骑上自行车沿村叫卖,曾卖到新乡、开封,以及山西晋城等地。“那时候年轻,”韩保领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白天卖鸡卖鸭跑一天,晚上回来还拉犁拉耙,还修建黄河引水干渠哩。”
1977年,村里组建了一个副业队,要远赴天津市电话局去架电话线、挖管道。大家都说他引黄干渠挖得好,推荐他带队挖管道去。他二话没说,就带着60多个年轻人上路了,算是周围村庄最早外出务工的一群人。虽然辛苦,但没少挣钱;逢年过节,没少给大家发米面酒肉等福利。农民还能发福利,周围村庄不曾有过,也算是从他这里开了个先例。后来,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一些穷家难舍的人开始陆续返乡。韩保领没回来。在天津那个大都市打拼多年,既历练了他的才干,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副业队解散后,他辗转到武汉、广州等地做生意去了,走南闯北的过程中,腰包渐鼓。2005年,事业有成的韩保领在市里买了房子,把家眷接过去,准备安居下来。
但村里的人不让他安居。
镇领导和村民代表找到他说,他不在家的这些年,村干部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村子一直在贫困线下挣扎,发展不起来。村民代表里有当年跟他一起搞副业的,后悔得牙根疼,说要是中途不撤回来,也早该跟着他吃香喝辣了。眼下这些都不说了,全村的老少爷们都盼着他回村,重新带领大伙突出重围,蹚出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众望所归,韩保领又回到阔别多年的村庄。
村子似乎比先前更破了,街道上的坑坑洼洼也似乎比先前更多了。无论往地里运肥,还是往家里收庄稼,车子东倒西歪,人则一步一泥泞。连那些走村串巷的小商小贩,都绕开韩徐庄走。目睹着这一切,韩保领两眼潮湿,觉得纵使千头万绪,先把路修起来当属第一要务。没钱修路,他带头集资,让大家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就行。
韩保领一口气修了两条贯通南北的水泥路,后又在镇政府的支持下,修通一条东西走向的连接乡镇公路的水泥路。事情就发生在这条路上。
线路规划图纸上有六座年代不详的老坟。
绕开老坟,路要拐弯,影响施工进度不说,人力物力的成本也会凭空增加许多,根本承担不起。直接平掉最省事,但有伤风化,于情于理都行不通。即便是年代不详,即便是无人认领,那老坟里埋着的,一定是韩徐庄的祖宗的尸骨,妥善迁出去才是万全之策。“迁哪去啊?”韩保领自问自答着说,“咱当党员干部的,不说尸骨晦气这些迷信话,但坟头占地肯定是不争的事实,没人愿意叫迁,只有迁到我自家的地里。”
自家地里一下子冒出六座坟墓,可把韩保领的老伴、子女给气坏了。天底下有拾金拾银的,还没见过他这样拾尸骨的;有供佛供神的,哪有他这样供鬼的!当初一家人劝阻他回村他不听,知道此番怕也理论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吃一堑长一智,他们直接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动员起来了。大伙儿一听,都气得不行,都说非叫他咋着迁来的,再咋着迁出去,否则跟他没完。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讨伐队伍扑了个空,没能兴师问罪成。不巧又偏巧的是,恰在这节骨眼上,韩保领病倒在了工地上。拉到市人民医院一检查,竟查出他肺上长出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医生说再晚发现几天,手术怕都做不成了。这可非同儿戏,一家人谁也顾不上坟不坟、鬼不鬼的事了,得跟癌细胞赛跑,得赶紧请专家名医把肿瘤切除了。“都说肺癌要命,”韩保领自嘲地笑起来说,“但肺癌也能救命。要不然,真不知该怎么个收场法。这事已过去好几年了,我还好好的。也算是积德修福了。”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东
韩保领回村做的第二件事,是清理废旧坑塘,引黄河水进村,形成荷塘连片的湖泊。一个地方有了水,仿佛就有了灵性,眼看着草木葱茏起来,空气清新起来,村容村貌为之改观,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也为之一振。已经脱贫的养鱼大户张进兴说,越是在有心人眼里,越没有不可造之物。他现在承包的这片2公顷大的鱼塘,就是韩保领带着大伙清理出来的。当初他怎么也想不到,昔日这片比人还高的杂草下面,比石头还坚硬的碎砖烂瓦下面,藏着真金白银,藏着诗情画意,有一天会成为他脱贫致富的风水宝地。
张进兴今年56岁,也曾是村子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妻子体弱多病,患有急性耳聋症、眩晕症。所谓有病乱求医,他可没少北上南下地遍访江湖郎中,讨他们的“灵丹妙药”或祖传秘方。到头来,妻子的病没去,倒欠下一笔巨额的债务。张进兴身高1.75米,一度瘦得像根打枣竿子不说,还早早地被债务压弯了脊背。那天晚上,有邻村的债主上门。不知是因为酗了酒发酒疯,还是因为讨要无果发脾气,吹胡子瞪眼的,言语也不干不净的,句句带刺,字字扎心。要不是张进兴妻子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眩晕,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真不知对方会说出什么更难听的话来。
等那人离开,张进兴好歹安抚下妻子,人也累了,倒在一旁沉沉睡去。因为妻子时不时地发病,他连睡觉也养成了时不时地按一下旁边的习惯。但是那晚,迷迷糊糊中,他按了几次都有按空的感觉,一激灵醒来,竟发现妻子不见了。张进兴连喊几声没回应,拔腿就往门外跑。他家在村子西头,离他现在的鱼塘不过300米。夜色里,他远远看见妻子趔趔趄趄地走在前头,走向水塘,忙三步两步赶上去,一把抱住了她。
妻子在轻生的途中又发病了,身子打晃,脚步踉跄,要不然他也许就赶不上了。妻子在他怀里乱捶乱打,哽哽咽咽地说:“我活着也是受罪,孩他爹你行行好、狠狠心,快点放我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再拖累咱这个家了。”
“不!”张进兴热泪盈眶,紧紧地抱住妻子说,“孩他娘你别乱想,就是走,咱俩也要一块走。”
“说得好,”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要走就一块走。一块向小康社会走,一块向幸福美好的生活走。”
说这话的是韩保领。
先前有人来张进兴家要账耍横的时候,邻居给韩保领打了电话。他在赶过来的路上,又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没事了,那人已经走了。他清楚人都有隐私,也都有尊严,再赶过去怕张进兴的妻子再发病,不如好好想想办法,到明天白天再说。可回到家里,终是睡不踏实,又披衣下床赶过来,正好赶上这一幕。
这一幕衍生的下一幕是,就让这对患难夫妻向这片水塘讨生活。
引黄河水进村的生态效益已经凸显,社会效益也堪称理想,该开发一下它的经济效益了。恰在这时,范县第三人民医院派驻的驻村第一书记郭自红也开始来韩徐庄驻村了。大家一商量,一致了意见,既然张进兴家离这片水塘近,不如就让他承包下来,养鱼种藕。没有资金,村里先是给他争取了5000元的创业扶贫资金,又帮他联系了5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没有技术,村里送他去县里、市里免费学习,并请来技术人员现场培训。人多力量大,一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贫困家庭,就这样被一双双温暖的手拉出了困境。
2016年年底,张进兴成为韩徐庄第一个摘掉贫困帽子的人,被评为脱贫标兵。现在,张进兴的荷园鱼苗厂已颇具规模,也颇有名气,不仅本地的鱼塘多从他这里购鱼苗,山东、河北等地的几十家鱼塘也从他这里购鱼苗,每年收入四到六万元不等。几经摸索,张进兴快成养鱼专家了,曾经佝偻的脊背重新挺拔起来。常有人来向他咨询取经,或请他去给出了症状的鱼把脉问诊,他随叫随到,乐此不疲。他说,自己的经验都是免费学来的,理应义务帮助别人。张进兴告诉我,一开始他也养过成鱼,但成鱼投入大,收益慢,不确定因素多,后来就专门养起了鱼苗。鱼苗吃得少,长得快,等到能吃的时候,也该转手卖掉了。有一种叫青鱼的鱼苗,可长到十几斤几十斤,进价每斤五六元,养到半斤左右的时候出售,每斤十四五元,中间差价七八元。所以,他是越养越有经验不说,还越养越带劲儿。“鱼苗欢实,”张进兴说,“就像小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地东奔西跑,看着喜庆。而且,咱的鱼苗好养活,不用担心销路。”
“张老板的鱼苗不是吃激素饲料长大的,”一位来自河北馆陶的田姓老板说,“皮实,健壮,适应能力强,成活率百分之百。不像有些吃这剂那剂长大的鱼苗,进一万尾,一换水就可能死几十上百尾。剩下的,也明显营养不良。它们吃惯了带激素的饲料,胃口刁了,很难调养。所以路再远,我们也来进张老板的鱼苗。”
“是党和政府把咱从泥窝里拉了出来,”张进兴说,“帮咱建了这个鱼苗厂,咱可不敢耍小聪明,贪小便宜,坏了党和政府的名声,坏了韩徐庄这个荷乡的名声。”
大嫂采芙蓉 溪湖千万重
在韩徐庄,人们说起香菊,必说到翠敏,也必说到翠华。乍一听名字,直觉上就是三个亲姐妹,实际上姓氏不同,分别姓程、姓史、姓胡。她们同为韩徐庄的媳妇,同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也同为韩徐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迹近的身份和命运,使她们结下不似姐妹、胜似姐妹的感情。
“说起来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香菊说,“那时俺仨的孩子都还小,公婆的身体也不大好……”
是一个雨季。男人都打工走了,她们三个留守在家中。因为住得近,彼此常互相走动。那天正说着话,香菊家的房子漏雨了。她俩帮她挪了床,又移了橱子,这里接上盆,那里接上桶。刚想歇口气,转脸看见翠敏掐的草辫子不知啥时候被扯断了,麦莛子散落一地。又一转脸,看见翠华的针线筐也不知叫谁踩翻了,还没纳好的鞋底溅满泥巴雨水。香菊深感过意不去,忙蹲下身子去收拾。“顾不上了,”翠敏一把拉住她说,“快一起跟翠华回家看看吧,她那儿怕是也漏雨了。”
冒雨跑去一看,翠华家果然也漏了。这一回,三个人都积累了经验,把该挪的挪了,该移的移了,互看一眼,不约而同地向翠敏家跑去。翠敏家的房子倒是没漏雨,但院墙倒了两三米长。雨一住,三个女人可有得忙了,和泥,搬砖,垒墙,砌瓦,把早先认为非男人不能干的活计,一一过了一遍手。忙碌的过程中,她们发现,三个人合起伙来,不仅有利于抱团取暖,还力气大增,还胆量大增,还不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也正是在给翠敏家垒墙的过程中,陪着郭自红入户走访的韩保领远远看见了她们,指指脚手架上的香菊、墙上的翠敏说:“就是她仨,好得跟一个人一样。”
顺着他的手指望去,郭自红看一眼香菊,再看一眼翠敏,明显凑不够数。正疑心韩保领是不是看花了眼,听见他又说:“翠华力气最大,一准在院子里和泥、递砖什么的。我们从门里进去,看到的就应该先是她了。”
转过门来,翠华果然比那两个人更忙,往脚手架上放几摞砖,再撂几铁锨泥,跑来跑去的,挥汗如雨。“我是个老瓦工了,”韩保领撸起袖子对郭自红说,“以前没少干这活儿。你先去别的家转转,我给她们垒垒墙。”
“既然赶上活儿了,”郭自红也脱掉外套说,“还转啥。我没有经验,让翠华升级上脚手架,我来给大家打下手吧。”
墙倒屋漏是最让人心凉的事,但这一次,因为两个书记的加入,三个憋着一股劲干活的女人,开始有说有笑了。就说到贫困户危房改造补助、创业扶贫补助政策,以及金秋助学行动等,特别说到一项改变三个家庭命运的大事:流转土地,勤劳致富。
2016年,陈庄镇积极对接市、县全域旅游的大格局规划,因地制宜,引黄河水进村入庄,在全镇范围内大力发展以“荷花观赏、莲子采摘、荷叶茶文化、休闲娱乐”为主题的生态旅游观光业。那时韩徐庄南头有一片8公顷大的土地,野草丛生,荆棘密布,蛇鼠出没,人迹罕至,因种小麦、玉米入不敷出,已经撂荒多年了。那天,两个书记给她们说的就是这片土地,并迅速给她们从镇上争取了每人2万元的创业资金。8公顷荒草,莽莽苍苍,蓊蓊郁郁,一眼望不到边,人走进去,连个影子也看不见。三个女人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像当初冒雨跑向墙毁屋漏的家园一样,不约而同地挥动镰刀斧头,毅然向这片荒芜砍去。
从此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从此顾不上品尝饭菜的滋味,从家里到地里,从地里到家里,一个比一个更脚步匆匆,一个比一个更风雨无阻。2017年,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左边荷叶田田,右边稻花飘香,泥鳅搅动的水声哗哗作响。三样收成算下来,虽然因经验不足赚得不多,一人只落万把块钱,但却如愿以偿地甩掉了压得人抬不起头来的贫困帽子,一一登上村子的光荣榜,成功跻身脱贫标兵行列。
这才叫人扬眉吐气。
三个人中,今年50岁的香菊年龄最长,辈分也大,翠敏、翠华喊她婶子。但拿主意的,通常是年龄最小的翠华,今年45岁。“翠华文化高,”翠敏说,“脑子也活,所以俺俩都听她的。”
听翠华的没错。今年,她们选取优质品种,改变作物连作习惯,在往年种水稻的地方种了3公顷莲藕,在往年种莲藕的地方种了5公顷水稻,没改变的,还是捎带着养泥鳅,结果种养双赢,大获丰收。同样的8公顷土地,不算还在收获中的莲藕,单是水稻、泥鳅两样收成,三人已一人增收了4万多元。
从不说撒肥时呛晕的事,只字不提薅草时中暑的事,压根不讲浇灌时滑倒在垄沟上的事,就像一次也没发生过多少次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事,但韩徐庄这个美丽乡村记得,三个大嫂忙碌在莲间稻田的身影,是它之所以构成美丽乡村最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也最感人至深。
1000年前,落落寡合的周敦颐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比如菊,又比如牡丹。但他独爱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进而发出“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的天问。往事越千年,我在韩徐庄看到,这里的数百名干部群众,无一不是他的知音。
莲之爱,同濂溪先生者众矣!
责任编辑:刘循源
新闻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