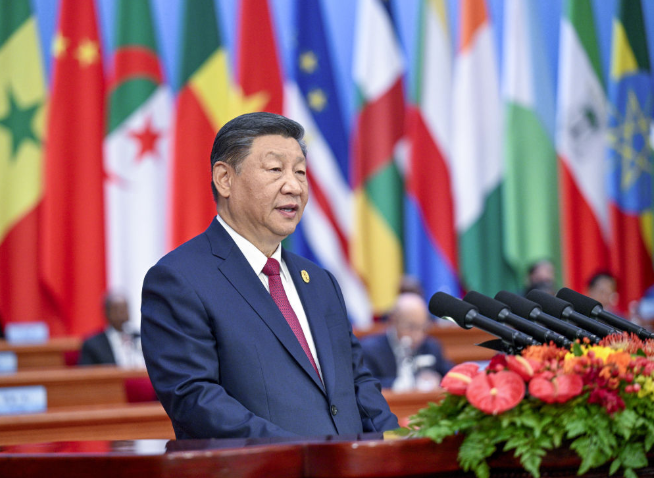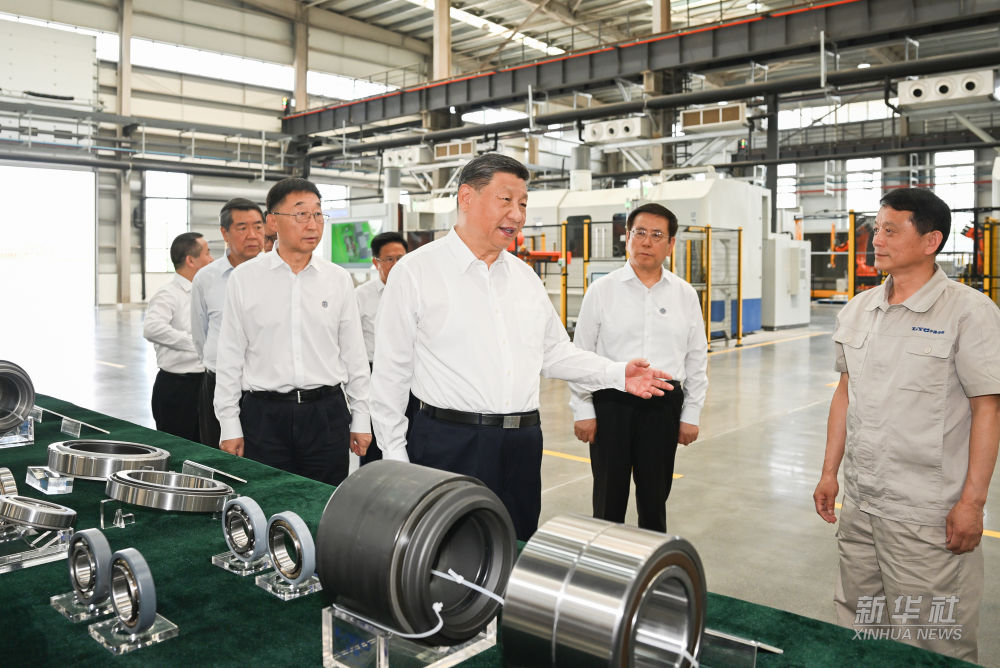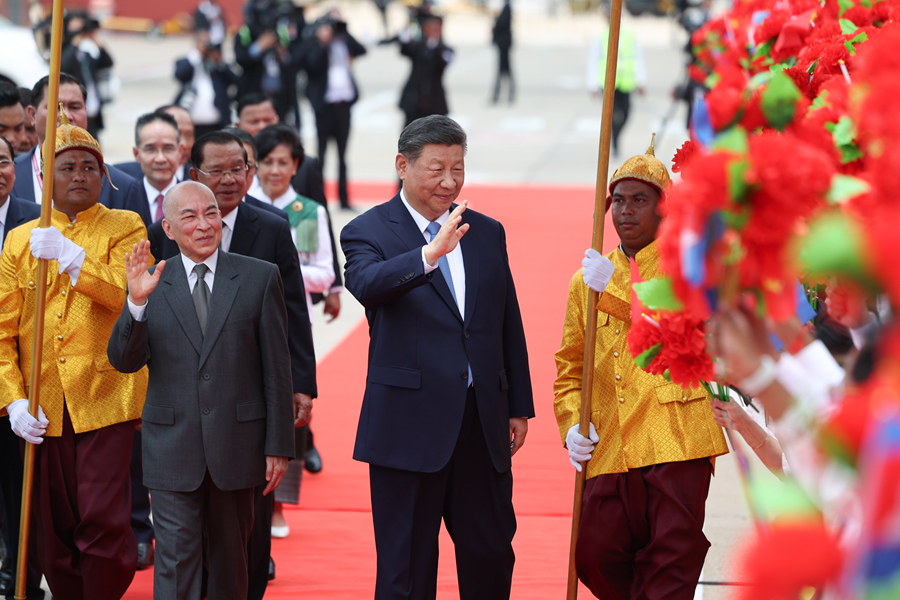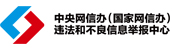铲除邪教为何难以斩草除根(图)

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时期的“宗教异端”、到元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再到民国时期的“会道门”,最后发展到今天的邪教,各种形式的邪教组织名目繁多,信徒少则几千人,多则达上千万人,其影响渗透社会各个阶层,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按照邪教教主的说法就是“欲兴作则大工可刻期而成,欲财货则千金可一呼而凑,一言传则一夕可以达千里,一令招则指日可以集万众。”并且,历史上的邪教组织在实力坐大,羽翼丰满以后,教主不会满足于自己在“神权王国”内的高高在上地位,开始觊觎世俗政权,无论公开或者秘密行动,都对社会和国家政权稳定造成极大的威胁,历代当政者无论是通过武力大举镇压,还是使用严刑峻法大力惩戒,或是通过群众运动人人喊打,但结果都只能将其消灭于一时而难以彻底根除。邪教组织这种“斩草易、除根难”的社会历史现象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拟从创教者和传教者的动机、信教者心态以及邪教组织自身的迷惑性进行分析,以期能够管窥其中的秘密,找出相应的防控对策。
一、历代执政者对邪教组织皆态度强硬、毫不手软
邪教组织的异端思想和各种非法活动,尤其是经常进行造反、暴动和起义,对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构成了很大威胁。明朝历史上基本是平均每年都发生一次造反或起义,而清朝一代邪教组织更是造反次数空前之多。
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参加白莲教反元大起义而得天下的,深知秘密教门对统治秩序的危害,立国之初,明朝政府就斩钉截铁的下令严厉查禁、镇压一切白莲教等“邪教”、左道。《明律集解附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就是说不分首从皆斩。清朝入关后,在《大清律例》中设立了专门打击秘密教门活动的条款。雍正三年修订的《大清律》中规定:“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者,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乾隆时期,处理教门案件时经常以“谋逆”为名重刑判处,为了防患未然,甚至对于一些慈善性教门干脆也一律加以取缔。整个清代,对于“邪教”中武装造反者,情节严重的援引“谋反大逆”罪凌迟处死;情节一般者,则依据“谋叛”罪,不分首从皆斩。对于一般敛钱者,则援引有关“左道异端煽惑人民”罪或传习“邪教”之律例,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发配黑龙江等地为奴,打压和防范手段可谓苛刻残酷。
尽管如此,清代教门的造反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影响较大的有乾隆三十九年爆发的“清水教”起义、乾隆四十二年甘肃的“悄悄会”起义、嘉庆元年到九年的“五省教门”大起义、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起义等。特别是为了镇压五省教门大起义,清政府花费九年半的时间,耗资2亿两白银的军费,死伤的提督、总兵以下高级官员400余人,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代价。

二、邪教组织难以斩草除根的原因
1、创教者为何而创教?做“生意”而已!传教者因何而传教?“一种职业和谋生手段”而已。
历史上的邪教组织,无论是创教者,还是传教者,不管其宣传口号如何“高大上”,究其实质,无非就是一门营生,一种谋生手段,一些传教家族尤是如此。如果说早期的创教者是为了改变自身经济拮据和社会地位低下处境而创教,然其继承者则把传教作为一种职业和发财致富的一种工具加以利用,子女继承教权无异于继承一大笔“家业”,故出现了大大小小众多的传教性家族,他们无不通过传教发财,富可敌国,如罗教教主罗梦鸿家族,黄天教主李宾家族,龙华会教主姚文宇家族,八卦教主刘佐臣及其各卦卦长家族,最典型的莫过于产生于闻香教教主王森家族。由王森创立的闻香教,从明万历初年到清嘉庆二十年,屡改教名,历经明清两朝,传承十代,前后递传200余年,传教范围达好几个省份。
当传教成为可以改善生计,甚至成为发家致富的一条捷径的时候,就会吸引众多的门徒参与进来。一些能量大的教徒,当自己在创教过程中日益老练,掌握的传教的秘密和技术手段后,多不甘心寄人篱下,任人摆布,则会另起炉灶,创立新教,自为教主。尽管每经过一次当权者的打压,一些大的头目消失了,而一些小头目或门徒会暂时蛰伏,继续藏身于民间,当生活困苦或不如意的时候,他们就会重新拾起“传教”这门耳濡目染的手艺来改善贫穷的状况。如雍正时期江西南昌大乘教传教者黄森官,靠做小生意为生,因开店铺折本无法生活,故传教骗钱 以教敛财,很快发家致富,富甲一方;乾隆时湖北襄阳收元教传教者孙贵远,石匠出身,因生活穷苦,时日难度,遂传教敛财,顷刻暴富。此种案例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民国时期,各种名目的会门道门令人眼花缭乱,大大小小的头目及普通的门徒仍然秉承着传教发财致富的宗旨,而相当多的且有一定实力的会首和道首则游走于各派军政势力之间,其控制下的会道门则成为攫取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筹码。甚至在当代,法轮功头目李洪志通过创立邪教法轮功获得亿万财富,即使被政府镇压后,逃遁在美国,遥控指挥国内邪教徒从事危害社会稳定和攻击政府的勾当。
2、信教者为何会“信”?
如果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也许不够严谨,但是如果说中国老百姓对信仰多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应该不会偏离太远,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信仰态度,再加上邪教组织对信徒开出的各种针对性的“药方”,很多普通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就掉进邪教的陷阱。
一是治病救人是邪教开出的最便捷、最有效的“良方”。疾病是困扰人类健康几千年的一个常见问题和无法避免的难题,特别是在医术不发达、缺医少药的年代,老百姓患病的几率更高。遍观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邪教头目,都曾经学过医,读过医书,有从医或巫医的经历,即使他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也会网罗会医术的人共同从事创教和传教事业。可以说,医术或巫医是邪教拉拢信徒的核心手段,在整个邪教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邪教头目每到一个地方传教发展信徒,最便捷的就是给当地的民众免费治病,民众病痛减轻或痊愈后,自然会对其感恩戴德,传教者借机对其进行拉拢。而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又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传教者混迹于其中如鱼得水,信徒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诚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所说,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即使是现在,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自然各方面的需求也会水涨船高。再加上当今环境资源、水资源、空气等污染,更多的新的疾病也发生在人们中间,故人们会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养生、健身之类的问题,一些当代“功法类”邪教正是打着强身健体、传播气功的幌子招摇撞骗,扛着如何健康饮食等养生的大旗诱骗人们入教。
二是给予实际利益好处是邪教开出的最直接、也是最实际的“药方”。一定程度上说,邪教组织也是存在一定温情的团体,教首剽窃儒释道教义,宣扬“向善”、“关爱”、“奉献”等思想,提倡信徒们之间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如罗教、大乘教针对粮船水手劳动艰苦,漂泊大运河上充满风险,收入微薄,漕运又有季节性等特点,在杭州、苏州一带建造庵堂,作为水手们回空时驻足之处,与老弱病残栖息之所,因而引得大批粮船水手皈依。而民国时期的会道门,如红卐字会、万国道德会等,也曾都兴办义学、进行赈灾、施诊施药施粥等慈善活动,特别是遇到水火疫病及迭次战争,组织救济队,赴灾区收容难民,救治伤员,掩埋尸体,建立育婴堂、残疾院、恤养院等,以救苦救难、从事慈善事业的面目出现。由于中国民众的宗教情感常常只停留在福祸相长的低等动机上,所以对于信仰所持的功利态度往往毫不掩饰。熟悉民众心理的教门领袖便采用一些不甚高明的小恩小惠的方法,诱人入教。当代邪教深谙物质力量对民众的吸引力。如全能神充分利用金钱和物质作为武器,对于女性,他们赠送高档化妆品、首饰及衣服等;对于男性,赠送手机、高档烟酒等;对于那些他们认为可能发展为“接待聚会”的家庭,更会斥以巨资,为其购买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空调等贵重家电;当他们知道某人欠人外债时,还会主动替他(她)还清。门徒会针对一些老百姓生活中的困境,提倡互相帮助,救困济贫,制定《周济工作计划》,称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是整个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正是由于所做的这些所谓的“善事”而使许多人“感激不尽,全家归主”。
3、邪教自身也披着美丽的“画皮”装点门面。几乎所有的邪教都披着宗教的外衣,从宗教中汲取营养,但他们又把自己凌驾于宗教之上,儒、释、道、基督、甚至民间信仰都是他们的营养源泉。明清时期的教门大都宣扬儒释道三教合一,而民国时期的会道门则声称“万教归一”。而当代邪教则更多的盗用了基督教的信仰术语,效仿基督教的活动模式,让追随者过读经、祈祷的生活,鼓励信徒“传福音”。而且还以为我所用、唯我独尊的态度对《圣经》任意曲解和歪曲,进行恶意的批判和取舍,利用了与他们有利的部分,否认了与他们不利的部分,挂羊头卖狗肉,蒙蔽善良民众的双眼。邪教教义中宣扬的一些内容表面上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李洪志在《转法轮》中说:“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门徒会的《六条原则》要求信徒“要忍耐、要和睦、改脾气、要爱人、要在家孝父母”。《十条诫命》中的说教也很“正”,要“孝父母,二十四孝传今古,在世长寿多得福;不杀人,不恨人,不骂人,不偷盗”等。中国人实用主义的信仰并不是出于对其教义的理解和理性的价值判断,而是追求今生今世个人与家庭的安定、美满、和谐,这就造成信仰的混乱不清,即凡是对保障生活幸福有用的神佛,都供奉和崇拜。而邪教为了发展壮大其组织,也臆造了一个所谓的“美好彼岸世界”,让加入者对此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幻想得到“幸福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对宗教一无所知却又渴望改变处境寻求精神寄托的人们很容易会成为邪教的牺牲品。
三、反邪教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
1、邪教组织形式的变异化和隐身化决定了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大都经历的不断地改头换面,譬如明代的“闻香教”转化为清代的“清茶教”。当代邪教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变异组织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全能神就是原“呼喊派”骨干赵维山带着一批成员从“呼喊派”中分裂出来,自立门户,变异出来的新的邪教组织。其他邪教组织诸如“灵灵教”、“被立王”、“主神教”、“门徒会”等邪教组都与“呼喊派”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2、邪教组织成员的知识化和高层化决定了反邪教斗争的复杂性。随着社会发展,邪教组织的成员也发生很大变化,当代邪教远远不是传统邪教成员那么简单了,一些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学历及高级技能的人员在当代邪教组织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有的还是邪教组织的核心骨干。如在北美法轮大法修炼者中,拥有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学位的信徒也不乏其人,从事的行业既有医学、生物学、化学研究的,也有搞电脑、通讯、遥感技术的,还有进行基本粒子、天文学和量子时空等基础研究的。这些高层次人员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使邪教组织更具有迷惑性,更有示范性,增强了其对抗社会的邪恶力量。
3、邪教组织经济实力的雄厚及传播手段的高科技化决定了反邪教斗争的艰巨性。邪教组织利用互联网宣传其歪理邪说,采用各种先进的通讯技术扩大和发展组织,高科技是把双刃剑,这把工具被邪教利用,危害后果可想而知。加之邪教组织敛财手段越来越丰富和成熟,邪教经济实力也越来越雄厚,打击治理邪教工作的任务将会更加艰巨。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邪教更是包装精美,裹着糖衣炮弹的鸦片。因此,要彻底清除邪教的毒瘤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防控打击邪教,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但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反邪教活动中,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决不可掉以轻心。
责任编辑:刘循源
新闻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