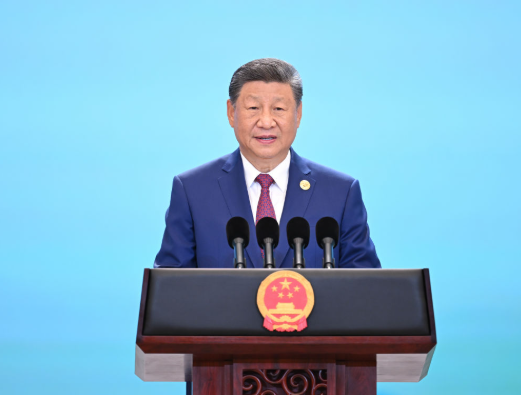医师节征文优秀作品选登——在援非的日子里
在 援 非 的 日 子 里
普外三科 白英伟

非洲,一个听起来让人生畏而又向往的地方。既让人联想贫穷落后、疫病肆虐,也让人联想到丰富的资源、旖旎的风光。我此生与非洲结缘,是因为有幸被选拔为中国第22批援非医疗队队员,于2020年12月初来到了“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不知不觉已9个多月时间,援非的日子历历在目,让我终生难忘。
埃塞是一个高原国家,平均海拔2000多米。刚到这里的时候还真不适应,强烈的光照让人睁不开眼,颠簸的道路让人呕吐,民族冲突和派系斗争催生的战乱让人心惊胆战,接着是水土不服出现腹胀腹泻。出发的时候国内的抗疫已取得战略性胜利岁月静好,而出了国境才知道“全球山河一片红”。
经过酒店隔离和核酸检测,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受援医院是一所名叫“提露内斯—北京医院”的公立医院,位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中国政府援建2012年投入使用的,主要收治当地的病人,是方圆几十公里最大的医院,所以病人非常多。
过去一年多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埃塞也没有幸免,所以疫情防控始终放在第一位,上班穿隔离衣,带N95口罩,带面罩的帽子,下班回来队员们脸上都会勒出一道印记。今年4、5月份埃塞的疫情非常严重,虽然我们在国内培训了消毒隔离、自我防护和疫情防控、医疗救治方面的知识,但是面对比国内严重得多的疫情大家心里还是很胆怯。提露内斯—北京医院虽然不是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但由于首都定点医院床位紧张,很多新冠肺炎患者无法转出,只能在这里治疗,致使本院很多医护人员感染。在这种严峻情况下,我们援非医疗队员被分配到不同的科室,坚持门诊、查房、手术和医技检查正常值班。在这期间,国内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不定期举行远程讲座,培训相关知识,医疗队严格管理,队员们相互关心、相互提醒,到目前全队保持了零感染记录。我本人还全程参与了我国政府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组织的“春苗行动”,帮助在埃中国公民和埃塞政府官员注射新冠疫苗,受到了大使馆和埃塞俄比亚中国商会的表扬。

在提露内斯—北京医院,我们的患者主要是埃塞居民,也有一些在埃中国公民找我们看病,无论是语言交流还是医疗技术,他们还是更信任我们。有一位患巨大腹股沟疝的中资企业员工,由于疫情影响已经近2年没有回国了,疝气反复脱出,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在我们刚到埃塞还在酒店隔离时,他就联系到我,希望我给他做手术。进入工作状态后,我了解到当地疝补片价格较高,这里大多选择常规疝修补术。这种手术患者术后的体验感极差,在国内已很少开展,经过我和患者的共同努力,我们从网上购买了疝修补片,协助他完成新冠核酸检测后顺利入院,为他做了无张力疝修补术,术后2天恢复良好,患者顺利出院。据本院埃塞同事讲,这是该院第一例无张力疝修补术。
甲状腺疾病和胆囊结石是普外门诊成年女性最常见疾病,多发性结节性甲状腺肿最多,几乎每次门诊都会看到很多例。由于医疗条件限制,来医院要求做手术的一般肿瘤都比较大,每周都要做好几例这样的手术。据了解,埃塞女性甲状腺疾病高发的主要原因是碘缺乏,回想我们国家强制推行加碘盐已经几十年时间,很多碘缺乏疾病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吧。
我手术的一位60岁妇女甲状腺肿瘤直径已经超过20cm,这么大的甲状腺瘤国内极其罕见。术前我们充分评估,由于肿瘤超大,基本的解剖结构已经改变,手术过程相当困难,一直持续了2个多小时才将肿瘤切下。每次查房患者和家属都是面带笑容,流露出对我们中国医疗队员的友好与感激,淳朴而真诚。
由于埃塞人的高纤维饮食、高海拔生存环境等因素影响,在国内比较罕见的乙状结肠扭转在这里成了高发疾病,有很多因乙状结肠扭转导致的肠梗阻患者急诊入院。有不少梗阻时间较长,肠管出现缺血坏死甚至穿孔,只能行肠切除手术,有时还需要造瘘,病人术后生活质量较差。为了更多了解这种疾病,寻找治疗和预防的办法,我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撰写综述文章,和当地医生们交流、探讨,受到他们的好评。我还首次用内镜联合肛管减压方法治疗这种疾病,可以使很多需要急诊手术的病人转为择期手术,明显降低了并发症和死亡率,改善了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这里的外科常见病例还有阑尾炎、胆囊结石、消化道穿孔、乳腺肿瘤、消化道肿瘤、外伤等,在一次次和当地医生协同手术过程中,我们的临床思维及手术方法不断交流碰撞,我把国内先进的诊疗技术分享给当地医生,有时候我也由衷地佩服他们的高超技术,感叹他们能在器械设备及医疗环境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能够做出那么完美的手术。埃塞俄比亚经济落后,医院断水断电是经常的事情,尽管医院有备用发电机,但掉链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一次做胆囊手术,术中停电长达半个小时之久,恰好在结扎胆囊管及血管后,心中有点着急,还是当地同事有经验,麻醉师和手术护士用手机为我照明,我竟然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外科门诊在这里叫做OPD(outpatient department)或SRC(surgical referral clinic),大多数病人是从提露内斯—北京医院下属的医疗中心转上来的,类似于国内的三级诊疗制度。好多病人都是一大早就从家里赶到医院,看病对当地人来说非常不容易,做个医技检查或预约个择期手术都要等很长时间。但是病人依从性非常好,医生在这里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医生出门诊,有一个护士专门负责登记、写处方、开检查单,然后医生签字。有两个类似分诊导医的人负责管理患者,排好顺序,依次看病。如果有入院的,她们会领着患者去办理住院手续。门诊病人很多,上午预约的病人有时候要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能看完,虽然很累,但是看到他们那种灿烂的笑容,内心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是阿姆哈拉语,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会说英语。我们在国内强化培训了英语,但是这里大部分病人根本不会英语。科室的早交班虽然是英语,但是非洲口音很重,刚开始多半听不懂,为了更好的沟通,我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外语,并学习了一些常用的阿姆哈拉语。现在交班已经可以完全听懂,当地患者的一些常见问题也能轻松应对。
埃塞是非洲54个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所以这里的人民骨子里带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善良、勤劳、热情,对生活充满希望,虽然物质资源匮乏,但是精神上很自信,积极向上。经过9个月来协作和交流,我和医院的很多本地员工成了很好的朋友。
刚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国驻埃大使的一番讲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援非医疗队员不是代表个人,也不代表所在医院、所在城市、所在省份,而是代表中国,我们是代表国家在向非洲传递友情,帮助非洲人民改善医疗条件,共享医学进步。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有祖国意识、家国情怀,维护国家形象。
我深知援非的重要意义,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在接下来的援非日子里,我将勉力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中国医生职业精神,用自己的技术给埃塞人民做更多的事情,讲好援非故事,维护中非友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冯牧羿
新闻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