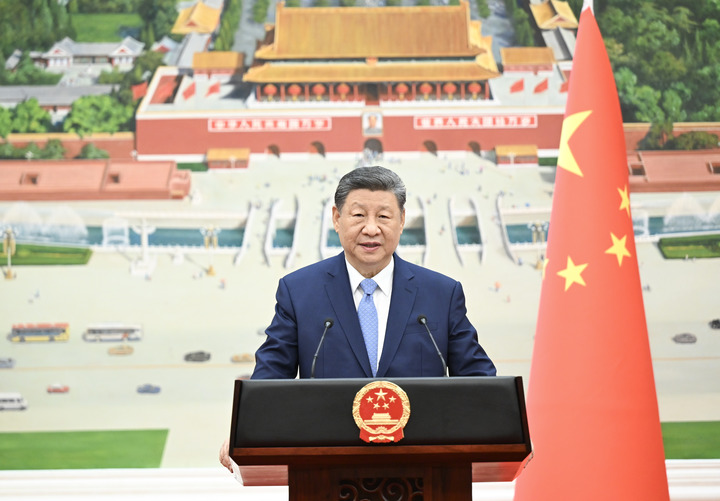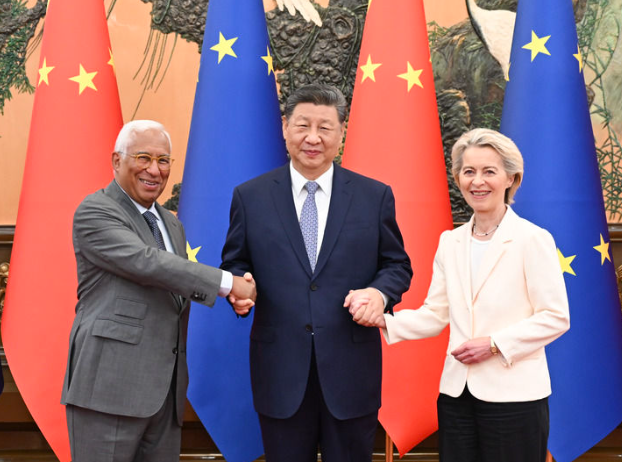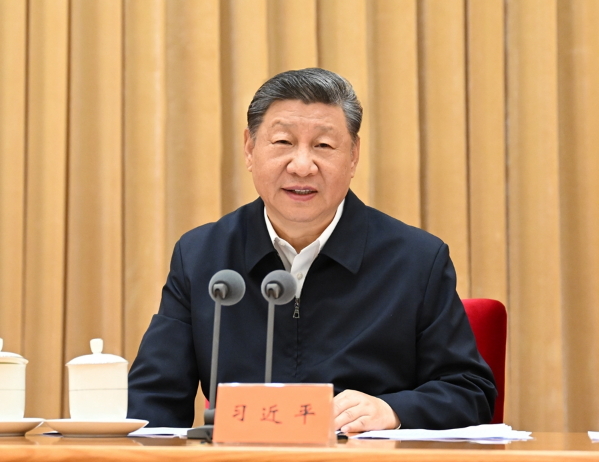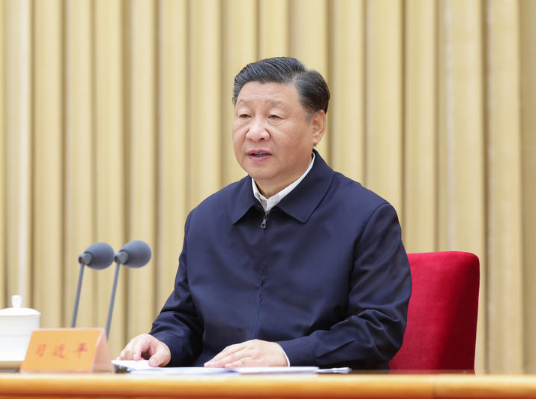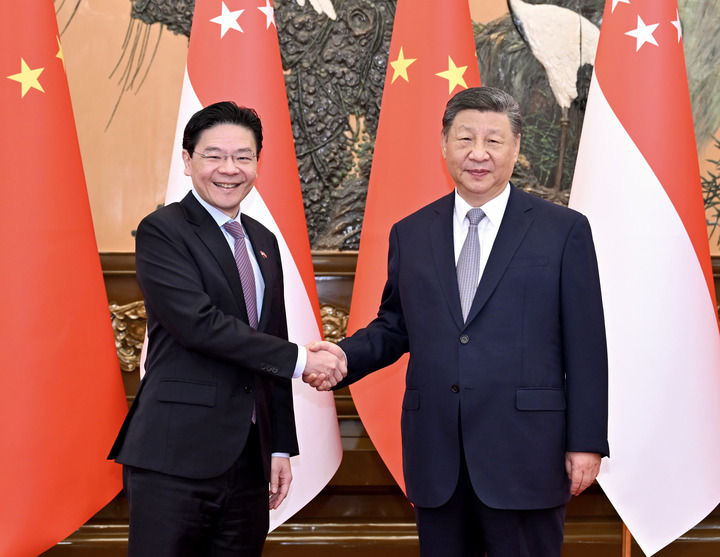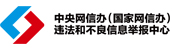黄天厚土
五月晚些的日子,枣花的清香将村庄打扮成芬芳的天堂,阳光从正南空旷的高处无遮拦地流泻到清纯如水的院落里。当麦鸟的叫声在村庄的壑旯里蹦来蹦去时,临近村庄田野里的麦子说黄也就黄了。从黄河岸畔刮来的溜河风懒洋洋地挥舞着金色的绢帕,被汗水浸泡的天空愈发做出一副深沉与尊严的姿态。
黄土地上的夏天是汗珠子滚太阳,拥塞的麦浪在一条条长方形的黄土高地里涌动着,像是在闹内讧或者风波,沉寂了多半年的黄河滩便平添了些许生计和活力。沿着时序的脉络一路北下的麦客潮汛般涌来,一个个古铜的面孔嘶哑的嗓音在狠毒的烈日下彰示着内心渴望丰收的激情,性格温润的黄土地便在那一刻开始沸腾。
等颗粒归仓了,麦收前丰腴的田野,这一片那一片被剃了头的黄土地上,刺棱棱的,显得很无可奈何,顿时憔悴萎靡了许多。秋收后的黄土地,再一次呈现麦子收割后的辽阔与空寂。蓦然回首。衣衫单薄的稻草人像是拾荒者,木讷地站立着,永久地守望着旷野,像是一个个颗粒无收的农民,在怅然中,等老了面黄肌瘦的日子。稻草人随风舞动的水袖如生命的旗帜在往事的黄土地上猎猎作响,在忧伤的眺望中飘荡着难舍的眷恋
闲来没事时,掰着脚趾头细细琢磨一下,黄土地的春耕和秋收其实就是一个潮涨潮落的过程,潮涨潮落,循环往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着装朴素的乡亲们走进远古的牧歌里谦卑地躬下腰身,捧起在心上祭典了很久很久的弯月把一束一束的阳光拢进怀里,拢进梦里。然后,便睡成田埂上一块憨厚的泥巴,依隈着风飞翔的羽毛入梦。
躺卧在黄河岸畔的村落从秋后到整个漫长的冬季都处在一种萧瑟土黄之中,所有的房屋和院落都是土坯垒砌而成。土地的黄色是黄河中下游地带的主色调,夹杂着湿汽的南风刮来时,弥漫着浓重的黄土气息和麦田的香气。空气中飘着杨絮,像秋后的蒲公英一样,散漫而恣意。南风刮来时,会从黄河滩上带来皑皑的尘土;北风刮来时,会从村庄的角落里带走皑皑的尘土。南风和北风拉锯般的保持地基的持平,像北李村三百上下的人口,生老保持水平。无处不在的黄土随过路的风不经意间穿堂入室,一点也不生分地落在它想落的地方,像个常来常往的乡邻。
到处是黄土的村庄里,铺路根本不用铺沙垫石,平铺直叙的黄土一遍遍地被人的脚印和家畜的蹄印给踩踏结实了,便成了路。这种细沙在阳光下闪烁的黄土路光滑平整,赤脚走起来惬意极了。尤其是在微雨淋漓之后,黄土贪婪地吮吸着细密的雨点,松散的浮沙磁实了,没有丝毫的水痕,但路面还略带一点柔腻酥软,好像海绵上铺了一层胶,如同面团一般,粘连性很好,踩上去不伤脚,走起来特别舒服。
黄土地上整日与像黄土烈日为伍的乡亲们,早已习惯在飞舞的风沙里行走,习惯了粗砺砺的溜河风划在脸上的感觉。他们有着和黄土地一样酱紫色的皮肤和麦黄的脸庞。他们粗糙的大手扶持着曲颈犁耕耘着贫瘠的黄土地,粗旷的嗓门吆喝老黄牛的“驾驾、喔喔、噫噫”声是方圆四邻八野都能听见的大秦腔。侍弄黄土地里的庄稼,不慌不忙间,自有一份与世无争的恬淡和宁静。无论黄土地承载着怎样的负重,他们都会用豁达而大度的心默默地去承受。夜暮四合了,落日在地头边的杨树梢间隐匿,一切都暗下来了,暮色浓的快坍塌了,越来越浓的暮色就要把一个忙碌劳作的身影擦去。
可置身棘手农事其中,黄土地上的人们并未感到这种挥汗如雨的劳作有多么的沉重和辛苦。因为他们从事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他们平凡而充实的生活,为了维系简单的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为了传承一种被大都市与繁华所遗弃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为了生活而耕种,为了耕种而收获,为了收获而劳作,这种劳动的轮回看起来似乎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根本不用渲染劳动的神圣和光荣。尽管是粗茶淡饭,尽管是惨淡经营,尽管是广种薄收,他们也把单调的日子调节得有盐有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黄土地上最忠实的守望者。于是,安身立命于黄土地上的乡亲们,往往出生于以黄土为底色的村庄,一生便与黄土相依为命搀扶而行,一个耗尽生命火焰的纯朴老人,最终又悄无声息地伴着一株在黄河滩上茁壮起来的大树静静地躺下,被厚实的木板紧紧拥抱,植入那片生他修养生休的黄土地,在另一个世界守望着这个被树环绕的村庄和子子孙孙的快乐与忧伤。
我贴近村庄的有关劳动的场面,要是累加起来不计其数。里面盛产着茧花和汗水,与诗人笔下的诗情画意的劳动场面没有连带关系。在绵延近千米的庄稼地里,只能窥到那些春绿或是秋黄的庄稼,不见荷锄或薅草的劳力。往往要等到腰酸背痛,汗流浃背,我才会缓缓挺起腰身,一手擦着额头上淋漓的汗珠,一手握着刚拔起来的抓拉秧四处茫然遥探。
尽管看不见首尾的春秋劳动旺季,披星戴月般劳作的乡亲们早已忘却了脉络清晰的晨昏。司晨的公鸡都叫两遍了,还隐隐约约传来吭哧吭哧赶着排子车爬堤坡的动静。我也开始明白,为何他们的腰带上都捌着旱烟袋和烟葫芦,稍有余暇,他们便蹲坐在田埂上,他只能用袅袅的清烟来平和心中的百结的衷肠和愁苦。
抽完一袋烟后,把旱烟袋朝千层底上狠力磕碰几下。烟窝里的旱烟丝的余孽被清理殆尽,重新把烟袋捌在腰带上。用手撑着地,慢慢舒展着立起腰身后。粗布裤子屁股蛋那里就粘了两坨黄土印子,很抽象,很粗犷,极像印象派的画作。然而村庄里很多老人似乎对黄土没有丝毫的在意。身上的沾了泥点子,鞋底垫了厚厚一层泥泞,裤子屁股蛋子上沾了两坨坐印子也似乎毫不在意。我感觉那泥坨子颜色纯净,是黄河的颜色,是阳光的颜色,那泥坨子没有一点难闻的臭气,它质朴,像黄土地伸出的一张手,往庄稼人的身上印了个印子。
守候与逃离并存,忠诚与背叛齐飞。当一望无垠的黄土地上,长不出林立的高楼大厦,高昂的学费和娇美的新娘。当快餐时代的洪流席卷而来时,当土地如干瘪的乳房再也挤不出乳汁时,当财富漫天飞散时,黄土地的孩子便纷纷背叛了父亲的王朝。丢下锄头和镰刀,扛着蛇皮编织袋,乘坐南下北上的列车,驶向背离村庄的方向去寻觅不明朗的梦幻。他们是春天逆飞的雁群,改变了生活最初的方向,贫瘠的黄土地,让他们首先学会了迁徙。
诗意飞扬的芦花,沿着黄昏的视线浅浅飞翔。每个清晨,屋顶上袅袅的炊烟,像是大地竖立的一只只温柔的耳朵。远离黄土地的子孙们,无论你走遍天涯海角还是踏遍千山万水,但依然有黄土地里的一株狗尾巴草,一朵迎春,逼近的让你无法触摸。
责任编辑:刘循源
新闻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