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荆门望楚
<唐> 陈子昂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
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
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
今日狂歌客,谁知人楚来。

【鉴赏】
这首五律是青年陈子昂初离巴蜀,准备踏上广阔的人生新天地时的诗作。它是一首纪行写景诗,更是一首抒情诗。诗人的情感,就渗透在纪行写景之中。正是诗人那种昂扬奔放、明朗喜悦,对前途充满新鲜感和乐观展望的感情,使这首诗具有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一种青春的气息,体现出唐诗趋于繁荣昌盛时期特有的风貌。
题中的“荆门”,是楚之西塞,亦即巴蜀与荆楚的分界。对于初次离开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踏上新的人生旅程的年青诗人来说,“度荆门”无形中具有某种象征色彩,即象征着将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天地。诗中洋溢着的新鲜感、舒展感和喜悦感,正应从诗人的人生分界这个关节点上去理解。
首联写“度荆门”时的回顾与前瞻。舟行至荆门时,离巫峡已有数百里之遥,故说“遥遥去巫峡”;向下游望去,传说中的楚国章华台就在远方,故说“望望下章台”。两句句首“遥遥”,“望望”两组叠字,写出了舟行过程中离巫峡越来越远,想象中的章华台越来越近的感受。“巫峡”属巴,“章华”属楚,“荆门”正是巴蜀与荆楚的天然分界。如果说,“遥遥”与“去”透露了对故乡的依恋,那么,“望望”与“下”则表现了对前途景物天地的向往幢憬。
次联分承一、二两句。“巴国山川尽”,度过荆门,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巴蜀的奇山秀水此告别。这句不仅是对地理分界的一种说明,更是概写此行所历的巴蜀山川,包括雄奇险峻三峡在内,“尽”字中同样透露出与巴蜀山川告别的依依之情。“荆门烟雾开”,船未到荆门,远望两山对峙,但见烟雾缭绕,看不清前路;船过荆门,则烟消雾散,眼前豁然开朗,展现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开”字正传神地表达出“度荆门”后心胸豁然的那份舒展感和兴奋感。而这种豁然开朗的舒展感又和此前舟行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的险峻逼仄感正形成鲜明对照,“开”字的精切不移于此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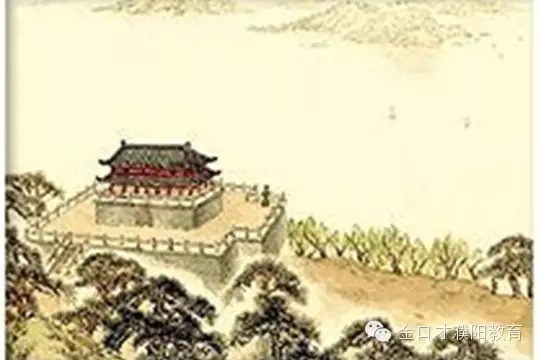
尾联是对“度荆门望楚”全部感受的集中表现:“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古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今有狂歌入楚之客,歌而过荆门。但“今日狂歌客”却显非昔日对现实不满的楚狂,而是对前途充满了美好憧憬的“狂歌”之“客”。“狂”字是对初次离乡“入楚”,走向人生广阔新天地的诗人欣喜欲“狂”的感情的集中揭示。诗写到这里,感情发展到高潮,诗也在“谁知入楚来”的逸兴飞扬、顾盼自得中结束。一结可谓淋漓尽致,神情飞越,颇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味道。用楚狂接舆歌凤典,单取其字面,且将“狂”“歌”“楚”三字巧妙地分置两句,表达与原典完全不同的感情。如此用典,可谓出神入化,巧手天成。知道其中用典的读者倍感其神妙浑化,不知道此处用典的读者也完全可以领会其神情风采,这正是唐诗雅俗共赏的一个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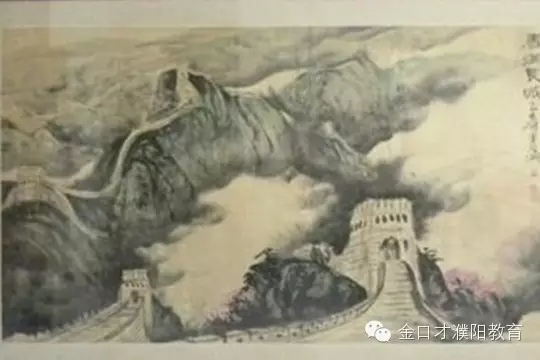
无独有偶,四十多年后的开元十三年(725),大诗人李白沿着前辈诗人陈子昂走过的路线,由蜀中沿长江出峡,到荆门时,也写了一首著名的五律《渡荆门送别》,其前幅云:“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其中所展示的开阔广远境界和所蕴含的开朗舒展感受与陈诗可谓神合。蜀地为四塞之国,虽号称天府之国,却因地理形势之故,相对封闭。因此志向远大的诗人沿江出峡,进入荆楚之地,当浩阔的山川天地展现在面前时,每有一种新鲜兴奋、舒展解放之感。陈子昂与李白,不但同为蜀人,志向个性也有神似之处。因此这两首辞乡出峡度荆门望楚的诗便同样具有上述感受。这种感受,也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来自大河濮阳)
责任编辑:李俊
新闻热点


























